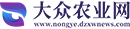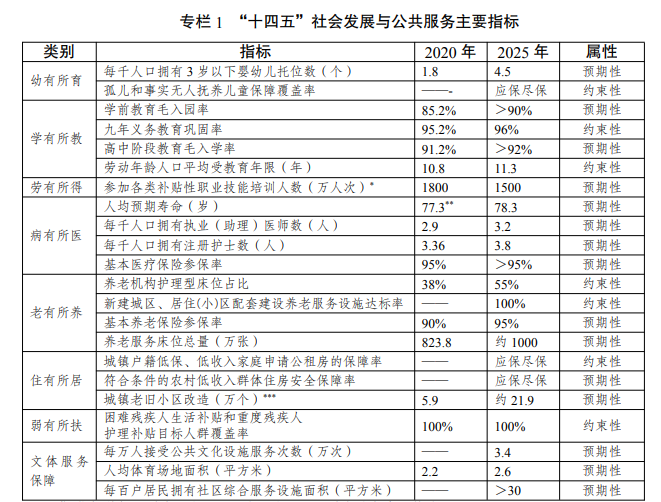图①:虞山以北的虞山桥边,立有虞帝的石像。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图②:位于桂林城北的虞山。
有史记载的桂林,多认为从秦始皇修建灵渠开始。但在灵渠开始运作之前,还能找到虞舜南巡百越的文字记载,这将桂林人类的文明史追溯到了四千年前。而从多方资料来看,有考古历史的桂林,实际上至少有三万年的沧桑。有据可考的桂林初民当属宝积岩人,但真正在考古史上留下更多印记的却是一万年前的甑皮岩人。甑皮岩人之后,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水位上升,桂林进入了一段洪水高发期,甑皮岩人也开始迁徙。
四千年前,桂林迎来了一件大事:五帝之一的虞舜帝南巡来到桂林。
大洪水时代的桂林
如前所述,一万两千年前的甑皮岩人在桂林这块土地上狩猎、捕捞、种植,绵延了五千年,但在七千年前的某一天,他们突然间就离开了曾经生活五千年之久的甑皮岩。他们去了哪里?
通过甑皮岩的考古,学者们认为,桂林先民之所以离开甑皮岩,也是迫不得已。
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岩洞已经不适合生存。
延续五千年的洞穴,所有的生活物资和生活垃圾都随手扔地上,一方面让后世找到了考古的路线,另一方面,他们让自己的生活空间越来越窄。七千年前,甑皮岩的空间也因此变得不适合氏族居住,最里面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甚至需要匍匐前行。五千多年前,甚至可能更早一些时候,大洪水时代来临,甑皮岩大部分时间处于被淹没状态。这种情况下,只能另谋发展。
可以说,大洪水从根本上改变了甑皮岩人或者说桂林先民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
关于古代的大洪水,有很多传说。
大多的大洪水传说是带有民族性并且多次出现的。现时,一个比较普遍认可的说法,是由于在七八千年前,全球的海平面曾经大幅上升超过一米。这一次海平面上升,使不少近岸及地势较低的地方都被水淹浸。这个看法所提供的时间节点,恰好与甑皮岩人离开甑皮岩另谋生路的时间吻合。
不可否认,目前人类在大陆上找到的大洪水的痕迹和证明并不很多,造成这一情况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大洪水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虽然各民族的神话记载不尽相同,但大部分的传说认为,大洪水仅维持了四十多天,然后退去,整个过程最长不超过一百二十天。这样短的时间,虽然对人类来说足够毁灭一次,但对地球地质来讲,还不足以造成很明显的痕迹。二是,大洪水距今有五千至一万年时间,岁月的流逝已经将本来就不明显的痕迹统统给抹去了。因此,不可能让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把一大堆证明材料都摆在你面前。不过,来自上古神话和有限的地质考古已经基本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五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段,确实发生过一场足以毁灭人类的大洪水。
这场大洪水,影响了全世界,也深刻影响了七千年前的桂林先民。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桂林,由于水位高企,除了猫儿山和海洋山外,大部分地区从地形地貌上看,酷似今天越南的下龙湾:浩渺的水面上,矗立着一座座具有典型喀斯特地貌特点的山峰,人们群居在山洞中,主要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生。此后数千年,水位仍有不同程度的反复,直到洪水全部退去,水位与今天相差无几时,桂林的部分先民才有可能进入平地,开始接受农耕文化。这个时间点,学界的看法是应该在四千年前,虞舜帝南巡到达桂林之后。
舜帝南巡到达桂林
七千年前,甑皮岩人开始了迁徙,此后,一直到秦始皇一统岭南,这段时间桂林的文明史几乎一片空白,人们的印象中,有文字记载、值得称道的桂林历史似乎就是从秦朝在岭南设郡才算开始。但实际上,即便没有形成城邦,没有国家,桂林这块土地上,也在四千年前就迎来了一件盛事:史称五帝之一的虞舜帝南巡来到桂林。虞舜帝的历史,有相当多的传说成分在内,但综合各方史料来看,四千年前的这段故事,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很大。
今天漓江市区段上游的虞山公园内,建有虞帝庙。官方网站上,关于虞帝庙有这样的文字介绍:虞舜帝晚年南巡苍梧,一路向南来到今桂林虞山下的韶音洞,宣传韶乐,推行德治,教化人民,从而成为桂林四千多年来和谐文化的开端,也是岭南地区各族和谐文化的开端……后来桂林人民怀念虞舜帝,就把此山命名为虞山。虞山东南山腰,还有始建于宋淳熙四年(1177)的南薰亭,可望漓江。后人怀思虞舜帝在山南立庙祭祀,称为虞帝庙,其始建年代已无从考证,在历代均有修葺。近年仿古重建。
虞帝来到此时的桂林,目的是宣传韶乐,推行德治,教化人民,从这些字眼来看,这个阶段,桂林的文明水平陷入了历史最低潮,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原文明,不然何须教化?这和甑皮岩人时代桂林先民不落后于中原的生产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个中原因颇有意思,值得历史和社会学家探讨。
据桂林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的资料统计:虞帝宣传韶乐的韶音洞以及山东和山南崖壁上,现存多达69件的唐至清代摩崖石刻,其中唐代1件,宋代6件,元代2件,明代29件,清代16件,无纪年15件,乃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似乎,秦始皇一统岭南之后,桂林在文明进展上的步伐又逐渐跟了上来。这也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我们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明形成过程,即中国多元一体化的民族大家庭格局,我们其实是可以这样认为的:在秦始皇统一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华文明在各地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同步形成。
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将中国文明起源地分为六大条块,包括桂林在内的岭南广西地区属于上述六大考古文化条块的一个支系,这个支系对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化的构成具有相当突出的贡献,我们至少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得到验证:
首先,最早学会制造陶器,桂林庙岩出土的陶片,经C14测定为距今一万三千年左右。另外,桂林甑皮岩也发现了早期陶片,以往认为桂林甑皮岩的陶器为距今九千至一万年上下,近年又在以往的地层下发现了更早的陶片,其年代与庙岩相近。另外,临桂区的大岩遗址也发现类似的早期陶片。同时,在相邻的湖南道县玉蟾岩也发现类似的早期陶器。这些地区都是古代岭南越人活动的地方,他们是早期陶器的发明者和使用者。
其次,最早学会饲养家猪,桂林甑皮岩发现有60余付猪骨架,经鉴定,大部分是经过人工饲养,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家猪实物。
这两种物质文化,是史前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标志。可以看出,此时的桂林,或者说甑皮岩人,其实并不落后于中原文明。
苏秉琦认为,文化是滚动性的,它们必然向各个方向传播。中华民族文明即是在这种流动的物质文化基础上滋生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文化一直是互动流通,并非“单向”。岭南文化向岭北流动,岭北文化向岭南传播这种互动的文化流向,并非从秦始皇政治统一岭南时期开始。岭南地区发现的玉琮、有段石器和铜卣、铜盘、铜鼎、铜钟等,都早于秦始皇统一岭南时间一两千年(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虞舜帝南巡到达桂林的真实性),它们都是从吴越地区和中原地区传入的。这就是考古学文化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不妨这么说,包括桂林先民在内的岭南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尽管岭南文明运动轨迹有其独立运行的一面,时弱时强,但又和中华文明运动轨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始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文明古国中的一员。
这个时期,岭南地区被称作百越(粤),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也就是从今江苏南部沿着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是古越人最集中的分布地区,非民族共同体。桂林也属其中。
资料显示,距今六七千年前,也就是甑皮岩人突然“消失”的年代,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开始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农耕和畜牧是当时主要的生产事业,在社会组织方面,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氏族成员以母亲的血统来确定亲属关系。
学者们认为,位居岭南的桂林,此时和中原地区还是产生了较大的区别。喀斯特地貌所造成的耕地稀少,让当时的桂林人并不擅长农耕和畜牧,打猎和捕鱼还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远古历史上,秦始皇一统岭南前,此时的桂林先民被称为百越民族的一支,史称西瓯。应该说,此时的桂林地区,从文明程度来看,与中原地区有着较大的差距。
■资料库
虞舜帝与韶乐
《竹书纪年》载:“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
《吕氏春秋·古乐篇》同载:“帝舜乃命质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由此可知,虞舜作《韶》,主要是用以歌颂示范为帝的德行。
根据《汉书·礼乐志》的记载,舜帝之后韶乐在陈(陈国)流行,到了春秋时期陈的公子陈完逃到了齐,所以把韶乐也带到了齐。韶乐是歌颂舜的德政的音乐,舜的天下平和,是由尧禅让。舜传位于禹也是如此,所以其乐平和。
因此孔子赞叹舜之乐是尽美矣,又尽善也。武王由于伐纣而得天下,其乐带有杀伐之声,所以孔子说,武王之乐是尽美矣,未尽善也。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入齐,在高昭子家中观赏齐《韶》后,由衷赞叹曰:“不图为乐至于斯!”“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史记·孔子世家·述而》)因而留下了一段佳话。
百越和西瓯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也就是从今江苏南部沿着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是古越人最集中的分布地区,非民族共同体。
《汉书》记载:“蛮夷中,西有西瓯,众半公式,南面称王。”《百越先贤志》也载:“译吁宋旧壤,湘漓而南,故西瓯也。”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有一支越人大部落活跃在浙江东部的瓯江流域一带,又有另一支越人大部落活跃在岭南、西江、浔江、桂林一带。为示区别,人们便称浙江一带那支越人部落为东瓯,而称在西江、浔江、桂林一带的那支越人部落为西瓯。
由于地理上北方中原与南方岭南距离甚远,先秦时期中原人与岭南人少有往来,以致先秦古籍文字上关于西瓯部落的记录寥寥无几。涉及西瓯部落的文字记录较为详细的是西汉史籍《淮南子》。
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临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百越军盟主)。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
据学者考证,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而广东地区文化经济水平可能高于广西,但政治实体较为松散。所以在秦始皇统一岭南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而在广西则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能统一广西及越南北部地区。
来源:桂林日报